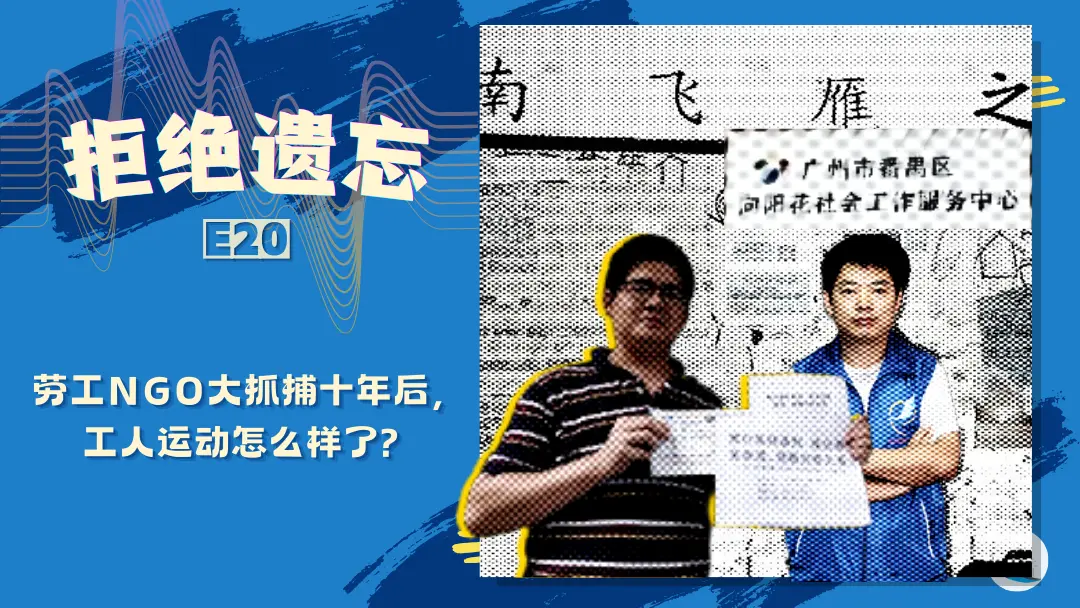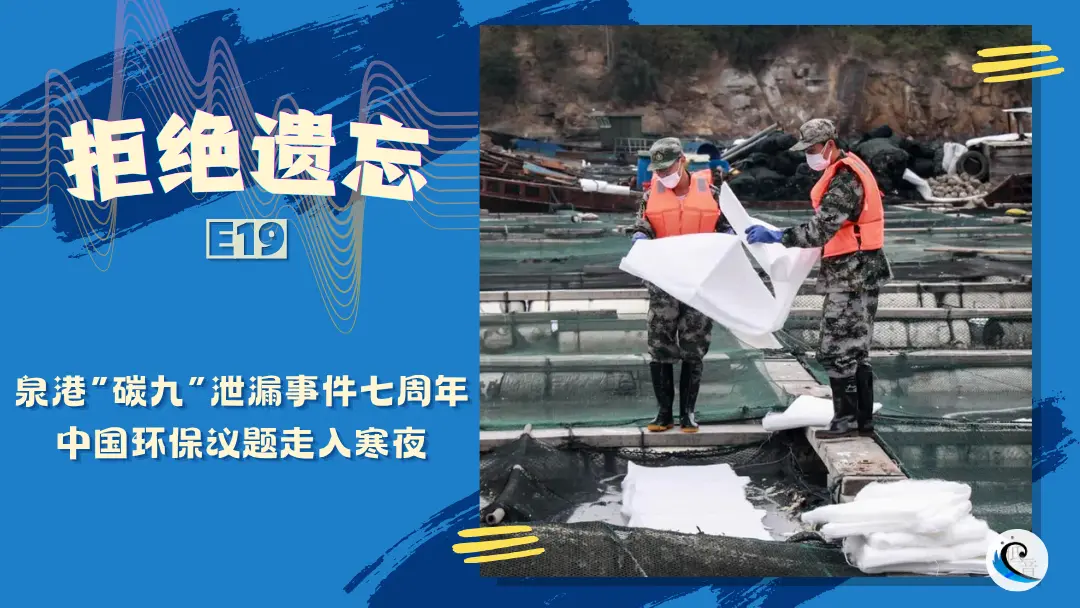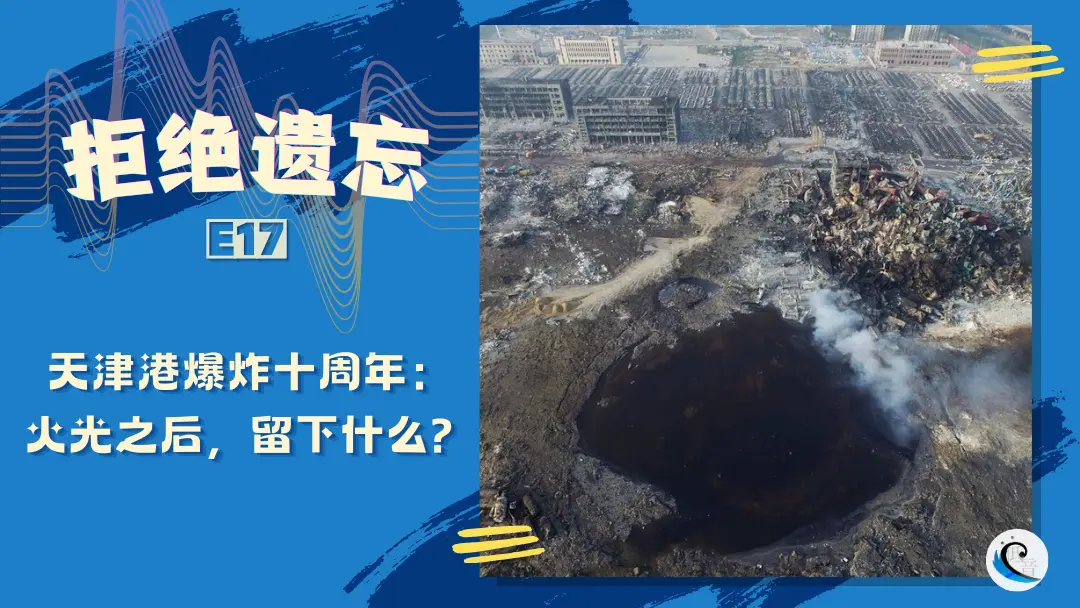本期内容简介
2015年12月,珠三角地区爆发了一场针对劳工维权组织的打压行动。数家为工人提供法律援助与维权支持的非政府机构遭到突袭,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被拘捕或软禁,罪名包括“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和“职务侵占”。这一波“劳工组织大抓捕”不仅是对个别机构的打击,更揭示了当时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的深度警惕与压制。在此背景下,曾飞洋领导的“打工族服务部”、佛山的“南飞雁”及广州的“向阳花”等机构成为了维权运动中的一部分,但随着打压的升级,这些曾为工人争取权益的组织纷纷遭遇重创,许多曾为工人维权的声音渐行渐远。
这一期《拒绝遗忘》,我们将回顾这场横跨十年的劳工运动变革:从这些非政府机构开始为中国劳工权益打拼,到它们因政策压力而改变生存策略,到最后彻底关闭,它们起起伏伏的经历反映了当代中国劳工NGO的发展历史。那么,这又如何塑造了现在中国劳工运动以及非政府组织的现状,这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思考,如今要如何看待几乎没有生存空间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它们和劳工运动之间的关系?希望这一期节目可以给你一些启发。
节目精彩时刻
- 00:01:54 撑起珠三角地区工人维权半边天的劳工机构
- 00:02:52 90年代工人处境:劳资纠纷时,工人往往只能忍受或是妥协
- 00:03:26 中国最早的劳工非政府组织,如何从发展走向末路?
- 00:06:22 获官媒称赞的“女工精神家园”,被列入“黑名单”
- 00:09:11 2015年,政府对公民社会开启全面扫荡
- 00:10:53 “全面服务化”的劳工NGO最终也未能逃脱被关的命运
延展阅读内容
- “向阳花女工中心”的《广州女工性骚扰调研报告》
- 《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是什么?
- “中国劳动趋势”报告:《从数据看劳工NGO的十年衰变:全面服务化、遭遇与遗憾》
播客文字版本
这一期,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个跨越十年的故事,那就是于2015年发生的劳工大抓捕。
2015年,对关注中国公民运动的人来说,我们更容易想起的事件是709律师大抓捕,又或者是“女权五姐妹”,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劳工领域,会发现这一年同样饱经动荡。
这个事件发生在2015年12月上旬。从12月3日上午开始至5日深夜,警察突袭了珠三角地区的至少四家劳工机构,至少五名工作人被拘留,他们分别是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下称“打工族服务部”)负责人曾飞洋和朱小梅、广州海哥劳工服务部职员邓小明、劳动者互助小组负责人彭家勇、佛山市“南飞雁”负责人何晓波。他们随后被刑拘,罪名包括“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或“职务侵占罪”。除此之外,还有多名工作人员及工人也被带走协助调查。
前面提到的这些机构和工作人员的名字如今听起来已经颇为遥远,但对于当时身处珠三角尤其是广佛一带的工人来说,他们几乎是撑起了工人维权的半边天。
打工族服务部负责人曾飞洋的经历最为典型。曾飞洋,1996年在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大专毕业后,回到家乡的司法局工作,后又“下海”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专门替企业客户解决各种法律问题。1998年初经手的一起案件,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当时,一个客户的厂里发生工伤事故,受伤工人被鉴定为五级伤残。按照法律,企业应向工人赔付10万元。但客户最多只愿意赔偿5万元。曾飞洋当时作为企业代表与工人进行谈判,结果却出乎意料地顺利。那时候,工人是势单力薄的一方,发生劳资纠纷往往只能忍受或是妥协。后来曾飞洋回忆说,这件事让愧疚在他脑中挥之不去,他觉得,工人们“本不应这么无助,是社会刻意忽略了他们对法律援助的需求”。
1998年下半年,他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当时刚刚成立的打工族服务部,后来接手了打工族服务部的工作。二十一世纪的头15年,打工族服务部作为中国最早的劳工非政府组织,在拥有数千万工人的珠三角地区,依靠法律咨询和维权协助等服务,逐渐在工人之中打响了名声。2014年至2015期间三次发生的利德鞋厂罢工事件,是这个机构参与维权的典型案例,但也成为打工族服务部后被查的导火索。
在这里,我们仅引用新华社在曾飞洋被捕后发表的《揭开“工运之星”光环的背后》一文,也能看出番禺打工服务部在维权中的作用。文章提到,2014年8月,利德鞋厂工人因社保、公积金等问题与工厂发生经济纠纷,随后曾飞洋对工人表示“帮工人维权不用钱”。文章提到,曾飞洋给工人们的第一印象是“温和、善良”,“曾飞洋免费提供培训,帮工人们了解法律法规,请工人们吃饭,还出钱组织活动和安排旅游;同时,要求工人选出代表,由‘服务部’与工人代表联系,再通过工人代表组织工人进行维权”。文章引述工人采访提到,“曾飞洋经常跟我们说,工人维权通过政府的途径太慢,不会成功,只有听从服务部的安排,把事情搞大给工厂压力,才会成功。”
而在这篇文章的定性中,打工族服务部被认定为:以“免费维权”为幌子、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在境内插手劳资纠纷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践踏工人权益的非法组织。
另一家被“扫荡”的机构“南飞雁”,全称是“南飞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立于2007年,其核心工作是参与工人工伤维权,也包括外来人口社区服务、流动儿童教育支持、流动妇女的生育保险等内容。有报道提到,作为佛山唯一的工伤维权组织,南飞雁累计协助过近万名工伤者。但在负责人何晓波被捕的两个月前,南飞雁就曾发布《此路不通,南飞雁公开信》表示,即使在佛山市政府批准了10万元扶持资金项目资助,也与当地救助站有社工服务合作的背景下,南飞雁仍然受压,可能关停。南飞雁工作人员在采访中说,政府“现在一直在给我们施加压力,此时我们现在还没有停止工作。但政府的意思是叫我们不要再做下去。”
有类似遭遇的,还有向阳花社工服务中心(下称“向阳花”)。此次大抓捕中,向阳花负责人骆红梅也被传唤后获释。骆红梅2008年曾遭遇工伤,经历了三年的艰难维权,后来在2011年创办向阳花,目的是给几乎没有业余生活的女工们提供学习和交流的空间,举办的活动包括语言舞蹈兴趣班、观影会、周末女工论坛、社区表演。2013年,向阳花曾针对广州女工做了一份《广州性骚扰调研报告》,指出70%的受访女工遭遇过性骚扰,报告引发了《南方都市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转发、报道。
向阳花也是正式在民政局注册的NGO,因为关注女工权益问题,还曾得到广东省妇联、广州市团委等赞赏, 省妇联甚至为向阳花的注册出资支持了5000元。2013年9月,李嘉诚基金会与广东省政府合作的“集思公益”支持妇女计划启动仪式上,骆红梅还在启动仪式上发言。但2014年之后,曾被官方媒体称为“女工的精神家园”的向阳花,就因持续介入多家工厂的工人维权行动被列入了“黑名单”。然后便是2015年的一连串打压——机构办公室被逼迁,工作人员被约谈要求自行注销登记,民政局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2015年,在骆红梅被带走之后,向阳花终于彻底关停。
这一轮大抓捕之中,多数被捕者在被关押数天到数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打工族服务部的曾飞洋则在被关押9个多月后,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另外两名工作人员当时已被取保候审,仍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半、缓刑两年。
从打工族服务部到南飞雁、向阳花,非政府机构参与工人维权在2010年代曾是中国劳工运动的主流做法。2014年,广州某首饰厂追缴社保公积金事件中的“首席工人代表”就在采访中说:如果工人维权想要成功的的话,还是离不开机构的帮助。它发挥了方向性的作用,就是它有很多策略,指明一个方向给你,起到了一个指路人的作用,你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它会提供解决的办法。
但在2015年的大抓捕过后,事情开始发生转折。这一年,正如我们在开头提及的,女权五姐妹事件、709律师大抓捕先后发生,政府对于公民社会的警惕酝酿已久,终于在这一年开启了全面的扫荡。与此同时,备受关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在当年4月开始公开征集意见,并在次年获得通过,由于严厉针对境外NGO在境内的活动,自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来涌现的民间公益机构,接收境外资助的难度也直线上升——正如打工族服务部的定性之中,“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也能成为一种罪名。
“中国劳动趋势”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就将这种变化称之为劳工NGO的“全面服务化”。报告引述数据显示,在2015年及以后成立的劳工NGO中,其组织目标已不包括“提升权益或改善环境”,而是一律的“服务与支持弱势”。服务对象上,2015年以前成立的劳工NGO中,有56.5%的服务对象为广义工人/农民工,而在新NGO中,这一比例下降至19.3%。报告认为,“在新成立的劳工NGO中,‘劳工’这一属性有明显的被模糊化趋势,转而代之的是公益、宽泛的属性。”
但后来我们会知道,“全面服务化”也没能逃脱房间里那只大象的碾压。2019年,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北京“冷泉希望社区”、深圳“清湖社区学堂”和广州“Hope学堂”三家以社区服务或职校生服务为核心工作的机构,被三地警方几乎同一时间突袭办公室。同在这一年被警察带走的,还有关注女工的机构木棉中心的童菲菲、心环卫的负责人祥子及两名志愿者。
后来,这些机构或是关闭,或是搬迁。清湖学堂在正式关闭的声明中说,“七年前,因富士康工人连跳事件,一批学生来此建设学堂,希望能改变工人的生活。七年后,他们亲手创立的学堂,也被迫自杀”。
一批倒下,又是一批,劳工机构成批倒下的十年之后,社交媒体上关于工人罢工、讨薪、维权的讨论依然持续出现,但关于抗争的想象,已经再难有工人口中的“指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