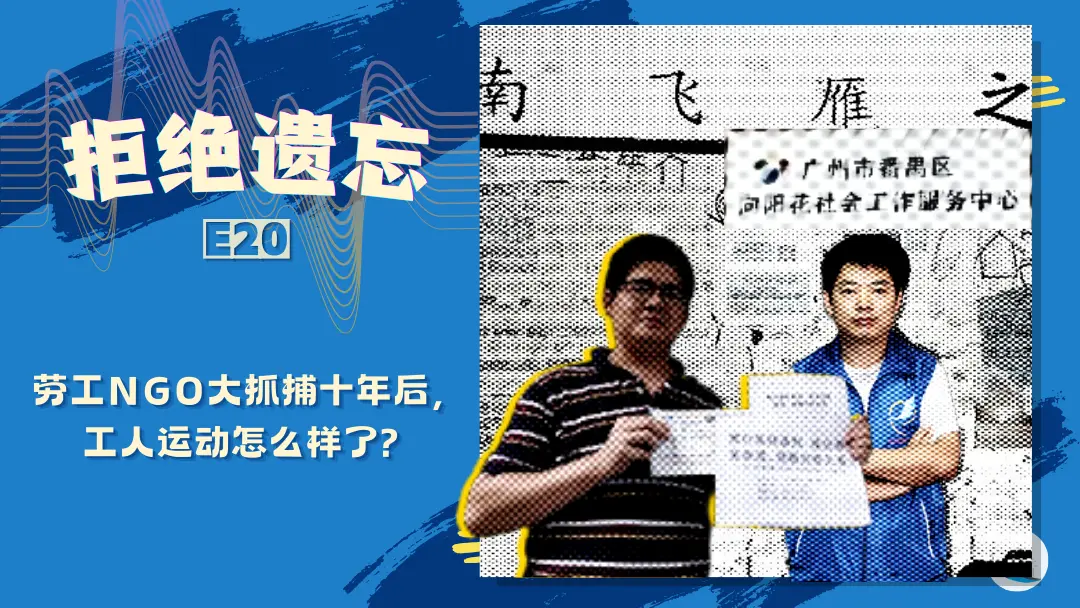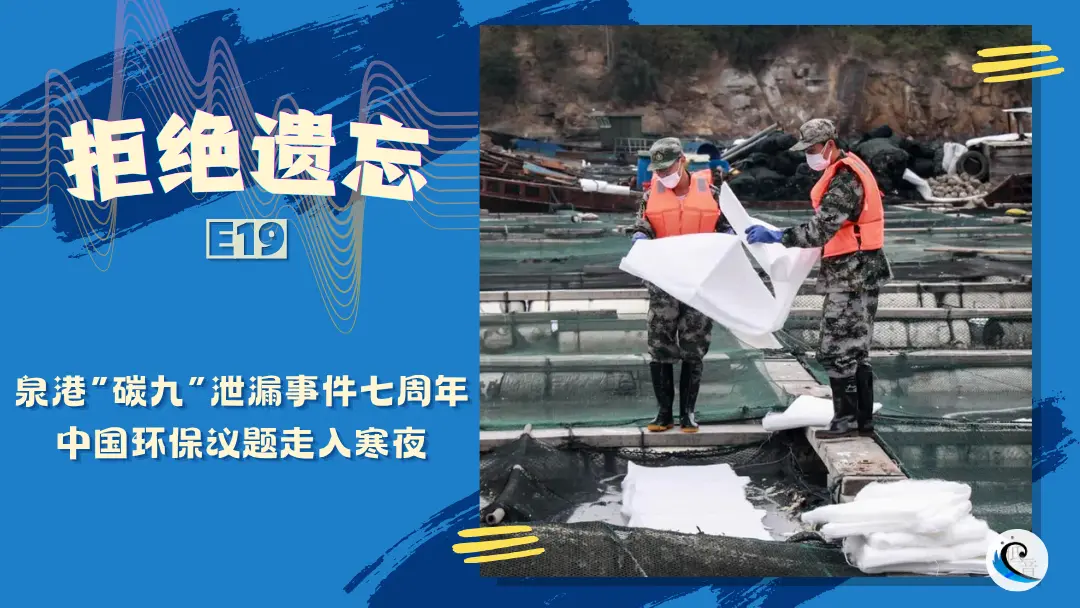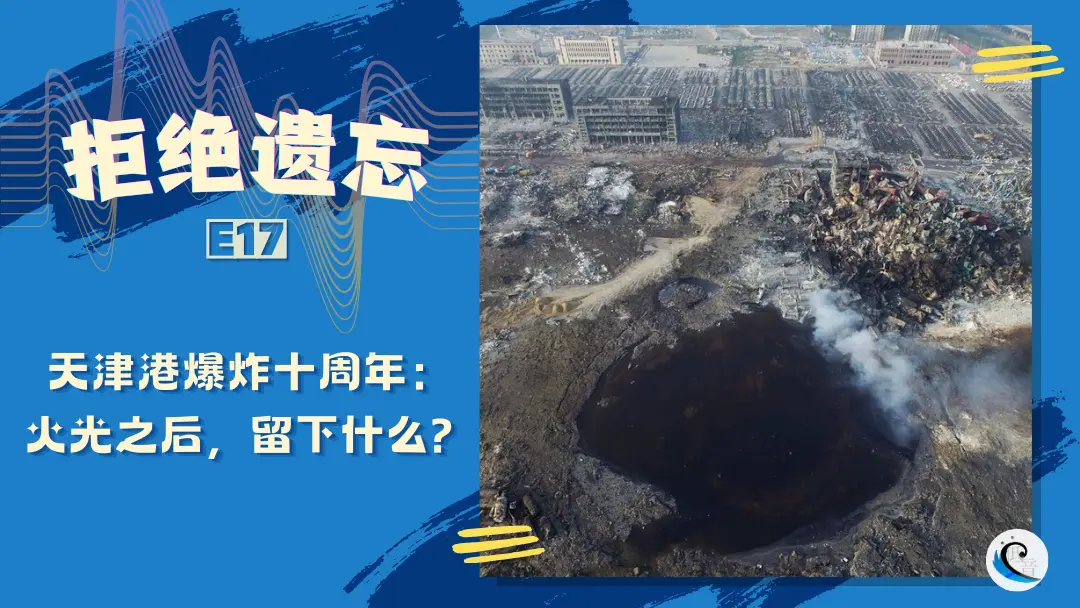本期内容简介
这一期,我们要聊的是维吾尔语。
今天是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低音请到了维吾尔语言学家 Abduweli Ayup,请他分享自己这些年保护维吾尔语言和文化的工作。他还分享了在中国的维吾尔地区,维吾尔语言是如何一步一步被“消失”的历史。维吾尔地区的现状非常让人忧心和痛心,为什么保护当地人的母语如此重要?希望听完这一期节目,你也有所感触。
本期节目嘉宾
Abduweli Ayup,维吾尔语言学家、活动家和诗人。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和新疆大学学习,后在美国堪萨斯大学获得语言学硕士学位。他曾在喀什和乌鲁木齐创办维吾尔语幼儿园,因推广维吾尔语被捕入狱。2015年流亡土耳其,致力于记录维吾尔人遭遇。自2019年起,他作为 ICORN(International Cities of Refuge Network)的驻地作家,现居住在挪威卑尔根。2016年9月,他创立了“维吾尔帮助”(Uyghur Hjelp)组织,记录维吾尔人的经历。他还出版多本儿童教育书籍,推动海外维吾尔母语教育。
节目精彩时刻
- 00:01:24 为什么要去捍卫维吾尔语,一门“濒危的语言”
- 00:03:27 “给维吾尔农民念《新疆日报》,ta们却听不懂”
- 00:08:34 2007年的乌鲁木齐,没有一个维吾尔语幼儿园
- 00:10:00 女儿到美国后半年忘记维吾尔语——原来“语言会死亡”
- 00:12:51 困难不断的语言保护工作:在巴黎被取消演讲、质问和跟踪
- 00:17:28 为什么语言保护的工作要侧重儿童教育?
- 00:25:00 维吾尔语是如何一步一步在中国被“消失”的
- 00:37:32 成立70周年的维吾尔自治区,现在是什么样的?
- 00:41:34 寄宿幼儿园,让维吾尔族孩子从小和母语隔绝
延展阅读内容
- Abduweliayup.com
- Abduweli Ayup. (2025). “A Thornbush in the Desert: Memories of a Uyghur political prisoner. "
- Abduweli Ayup. (2024). “China: Hundreds of Uyghur Village Names Change.”.
- Abduweli Ayup. (English translation forthcoming in 2025). The Black Land. Selkies House Limited.(现已出版维吾尔语和土耳其语版)
- 纪录片,"Behind the Mask” (2023, Håvard Bustnes)中,讲述 Abduweli Ayup 从新疆到挪威的逃亡经历
- Steven Pinker. (1994/2007). The Language Instinct.
播客文字版本
低音:就在今年初,2025年2月,Abduweli 受邀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参加一个语言会议。但就在开会前不到24小时,他突然接到通知,他的发言被取消了。在和我们的分享中,他屡次提到这些年捍卫维吾尔语言的重重挑战。那么,是什么启发他要去捍卫这门“濒危的语言”呢?
Abduweli:维吾尔语言文学是我的专业,我选择这个专业的原因是,我在喀什长大,我们那个乡叫做乌帕尔乡(Upal,ئوپال)。乌帕尔乡有一个11世纪的维吾尔语言学家,他的陵园在那里,Mahmud al-Kashgari。他编辑撰写第一部维吾尔语和阿拉伯语词典。那不光是一部词典,那里边包括民间文学,就是当时的一个百科全书吧,通过这个词典的方式,解释当时的人文地理,科学艺术。
我从小听到有关那个语言学家的故事,就觉得这个语言学很重要。第一次听到的科学,就是有关语言学,特别感兴趣,到北京来,就这个原因。因为北京有个维吾尔语言学家,当代的,他叫哈米提教授(哈米提・铁木尔,خەمىت تۆمۈر)。哈米提教授是创办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系的一个人,1951年到北京,在那当老师,然后培养自己的学生、自己的弟子创办了那么一个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和系。
我小时候喜欢看小说,有一部小说里面提到的他的名字,就提到他是一个成功的语言学家,在北京办了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然后我到北京上语言学,我97年毕业,毕业以后回到喀什。那个时候你不能自由工作,你就必须到被分配的地方去。把我分到喀什的一个村,一个乡,多来提巴格乡(音译),当翻译。
当时我们的工作就是给百姓讲座,讲什么呢?加强党政基层工作什么一个东西。我们每天让那些维吾尔农民到村支部来,就给他们念《新疆日报》。当时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讲的是维吾尔语,《新疆日报》是维吾尔语的一个报纸,但是他们听不懂,我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清楚。然后把报纸撂到一边,就讲它的那个内涵,用通俗的、我们日常生活使用的,小说里头用的那种维吾尔语来解释,这样他们可以听懂。
语言学上有这么个东西,“Diglossia”(双重语言现象,指在同一语言社区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语言形式或者方言,一种是高阶、正式的书面语言,另一种是低阶、口语化的日常交流语言),“di"是两个的意思,“glossia"就是语言。阿拉伯语有这个现象,比如说《古兰经》的语言(现代标准阿拉伯语或古典阿拉伯语)人家听不懂,普通人(日常交流的方言如埃及阿拉伯语、叙利亚阿拉伯语等)讲另外一种东西。古印度语也出现过这么个事情,梵语和印度语差别很大。中国也出现过这么个东西,白话文以前,新青年运动以前。
我发现维吾尔语出现了这么个东西。原因就是,《新疆日报》百分之百是翻译的。用汉文出版《新疆日报》,维文版是汉文版的翻译。新疆电视台也是,看上去是维吾尔语的,但是所有的新闻、社论,都是从汉语翻译过来的。所以《新疆日报》、新疆电视台、喀什电视台、《喀什日报》,全成了一个翻译的工具,不是维吾尔语。
那个时候我还是喜欢古文字、古文学。我觉得这个现实的问题太残酷了,我就研究一些历史东西、历史文献,这个比较好一些。我就开始研究维吾尔古代文学。我在新疆大学上了三年的古典文学的研究生,但是也出现了问题。
导师让我研究古代文学,通过马克思文艺理论,和毛泽东延安文艺理论blah blah思想什么的。我研究的人是十七世纪生活过的人,我就说那个时候马克思还没生下来,毛泽东更没生下来,这个怎么做?最终硬着头皮就同意了,因为不同意不行,我爸甚至过去赔礼道歉,因为我不听。
在喀什那个乡工作的时候,(要)搜索人家的房子,找危害国家安全的,危害民族团结的书什么的,搜书。我就说这个非法,这是人家的私有财产,我们不能随便进,这是制造矛盾的。
当时朱海仑是喀什市委书记。我就写了个请愿书,说那不是我们的事情,那是公安机关的事情,我们不是公安机关,我是翻译,我们是一个乡政府,我们不应该干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这是不对的。我写了“国家干部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应该履行警察的职责”。朱海仑当时很生气,他把我批评了一顿,他把我叫到公安局,然后我哥走了后门,行贿,才把我救了过来。
我就觉得新疆呆不下去了,我要到国外去。
但是我当时没有护照。在新疆办护照是特别麻烦的事情,比上天还难。然后我去兰州工作了,去兰州工作原因是要办护照,不是干别的。我申请了护照,然后去了土耳其。土耳其我待了一段时间也不习惯。因为土耳其也是一个社会等级制度特别明显(的地方)。我最讨厌的是在中国,人家互相拍马屁,在土耳其也是,特别官僚。
我就回去了,我有了孩子,到那个时候,我都没有关心维吾尔的现状,因为从喀什回到乌鲁木齐,我就专心研究维吾尔古代文学,在兰州也是教古代文学之类的课程,我对现实没有很多的接触。
我有了孩子以后才发现,当时乌鲁木齐没有一个维吾尔语幼儿园,都是双语幼儿园。双语幼儿园意思是什么呢?是汉语幼儿园,我就觉得这怎么回事?那是2017年(低音注:口误,这里指的是2007年)。还有我害怕没有给孩子清真食品。食品是统一批发的,你也不知道那个是清真的还是不清真的。然后我觉得这不行,我就准备开幼儿园,但是当时乌鲁木齐找不到合伙人。那个时候乌鲁木齐人已经习惯了,幼儿园就是汉语幼儿园嘛,没必要开个维吾尔语幼儿园,人家也没这个(指开维吾尔语幼儿园)意识。
然后我就很失望,哎呀就去美国了,就想再不回来了。那个时候是福特奖学金,在北京有个福特办公室,我估计是2012年结束了它的中国的项目。我申请的时候是2007年,2008年我成功,然后2009年我到美国去学语言学,那个时候我们请来了一个著名的语言学家,叫Steven Pinker,是一个语言保护的提倡者,又是一个思想家。那个人写了一本书,“Language Death”(低音注:口误,书名为"The Language Instinct”),《语言的死亡》,那个人恰恰到我们学校来办演讲。讲述语言怎么死亡,怎么失去,这些东西。
我联想到我的女儿。因为我的女儿在乌鲁木齐没有找到维吾尔语幼儿园,然后到美国来,6个月之内,把维吾尔语都忘掉了,忘得一干二净。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是三岁半,维吾尔语说得特别特别好。我就着急了,那样的话,那乌鲁木齐成千上万的孩子,都放弃自己的语言,失去自己的语言。我本来不是很感兴趣,汉语幼儿园就汉语幼儿园吧,但是我女儿在美国忘掉了维吾尔语,我就害怕了,维吾尔语就会消失。
就那段时间,我收到了邀请函去参加 Language Document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conference,国际语言记录和保存(研讨会)。那个研讨会选择了五门语言,作为重点记录的(对象)。那个五门语言里头,一门是维吾尔语,那五门语言都是濒危语言。It shocked me because I have never thought, Uyghurs is one of the endangered language in the world(我从来没想过维吾尔语是世界上濒危语言的一种,这让我震惊)。
然后我去在那儿待了一个半月。那段时间,七个语言学家就记录我的语言,我说什么都记录,就好像他们关注一个快要消失的、最后的一个维吾尔语一样。我就感觉我成了最后一个说这个语言的人。特别伤心。
这个学术研讨会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学到了好多东西。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我要保护我的语言,这个语言不应该这么消失。所以这个学术研讨会和 Steven Pinker 的书,和我的女儿的现实情况让我感觉到了保护语言的重要性,我决定要回去办幼儿园。
低音:他说“语言也是一种人权”,保护维吾尔语言的工作也是一种保护人权的工作。但是,即便在“人权宣言”发源地巴黎开展工作,他仍然面临着被质问、被跟踪的风险。接下来他分享了一个小插曲,提到他在巴黎分享自己的语言研究成果,却被参会的中国分享者跟踪,而没有受到活动主办方的任何保护。
Abduweli:我到巴黎参加那个国际语言与科技研讨会,我的题目是《维吾尔语和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我的文章有关维吾尔语和通讯技术之间的关系。我本来是被邀请做 speaker,上台演讲的那种。有一段时间他们说政治原因,把你的 speaker 身份取消了,我说可以。
他们请我去做poster presenter, present your research on the board during the coffee break or lunch break, not that official one(在茶歇时在展板上展示研究成果,相对没有那么正式)。我说可以,机会还是有的。
我去了,第一天早晨,有一个发言的是中国湖南卫视来的一个小伙子,他介绍自己是语言保护者,他说在中国语言保护特别好,有三十多个语言博物馆。然后我就提了个问题,三十个语言博物馆,那是挺好的事情,我的问题是你这三十个语言博物馆,包括维吾尔语、蒙古语和藏语吗?他就开始不自在了,就说新疆很美好,新疆很漂亮,大家到新疆去旅游、参观、玩。他的答案是这个。coffee break 的时候,那个小伙子过来,另外一个小伙子也过来了,三个女的也过来了,说,“你是新疆人吗?”
我说,“我是维吾尔族,但是我不知道说我是新疆人什么的。因为我是兰州人,按户籍来讲的话。如果按国家来讲的话,中国把我的护照取消了,这意味着我没有国籍,那我是挪威人。如果是人种来讲的话,我是维吾尔族。”
他说:“你在中国有没有兄弟姐妹?”
我说:“有,但是他们已经被判了,他们已经在监狱里头。”
他说:“你在撒谎。”
我说:“那你给我撒一个,编一个东西。让你的大使馆去查去,我兄弟姐妹在哪里,他们的身份证号我都有,他们地址我都有。”
他说:“你有没有证据?”
我说:“我有证据,那个‘新疆警察文件’曝光了。”
他说:“它都是假的,都是西方炮制出来的。”
我说:“两万九千人的身份证号,家庭地址,就那些东西“。
就那样辩论一番,然后我就不想跟他们再聊了,就回去了。然后那个小伙子就跟随了我三天,在那里,我做什么事情他就在后面拍摄。很愤怒,因为有人跟随你不是一个好的感觉。
就在巴黎。巴黎是什么地方?巴黎是“人权宣言”的发源地,不是美国是在巴黎,人权这个词就在巴黎发明的。It’s unacceptable,当时我就特别生气。(对)联合国那些人我都说了,你们在干什么,我们在法国领土,有人跟随我,你把我的演讲都取消了,这是怎么回事?
当时我们的组织者,领导是日本人,日本的一个语言学家,他们一个都没有发声。
低音:Abduweli 保护维吾尔语言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和孩子们一起完成的。他办过维吾尔语的幼儿园,编写和出版过维吾尔语的儿童读物,他和我们分享了为什么语言保护的工作要侧重儿童教育。
Abduweli:因为幼儿园起关键性作用,人3岁到6岁,如果掌握那个语言,掌握得好的话,就不会忘掉。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回去办幼儿园。我就开始在美国我女儿上学的幼儿园去实习,然后我学了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是儿童语言系的课程,然后学儿童心理发展课程,(学)中国孩子怎么习得语言,美国孩子怎么习得语言,日本的孩子怎么习得语言。
2011年6月份,我回到乌鲁木齐,然后回到喀什,就办了两个幼儿园,在乌鲁木齐一个。在喀什先办,在喀什的是2011年9月15号办的,在乌鲁木齐的是2012年的9月份。我们乌鲁木齐的幼儿园被封闭了,当地的教育部门不允许我们开。然后我们在网上发起 Campaign,行动,要求当地政府批准我们开维吾尔幼儿园,然后我们一下子有了150万的 followers。维吾尔人特别愤怒,怎么连幼儿园都不能办?
2009年的“七五事件”让维吾尔族觉醒了,叫醒了,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这个民族会消失。全社会就掀起了保护维吾尔语的行动,比如说维吾尔语方面的书出版的很多,有人写了诗,歌颂维吾尔语的,甚至出版了一本书,把歌颂维吾尔语的那些诗歌都放到一块,就是两百多首诗呢。就那样。有人拍了纪录片,也有人拍了电影,也有人办了相声。我特别感动,当时觉得我做的这个(是)好事情,这是维吾尔人都关注的,都能参与的这么一个活动。
但是150万 followers 不是小数字,这是一个。第二个,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我就开始害怕了。因为如果有这么多的人跟随你,支持你的话,共产党不会高兴的。开始威胁,开始跟随,开始经历喝茶,甚至逮捕我。最终我们被抓了,我和我的三个同事都被抓,我们三个人被判了。2013年的8月19号,我们都被抓 、被判了。另外的那个小伙子没有被判,但是他2017年被抓了,判了20年,所以这个语言保护运动到此为止。我在监狱待了15个月,他们提前三个月放了我。
我在监狱里头见到好多好多人被抓。我当时被抓的时候,一个监室有16到20个人,我出来的时候,一个监室甚至有30、35,快40个人都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好,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决定要离开。我不离开也不行,因为我有那个犯罪记录嘛,在喀什我待不下去,因为我的户口没有在喀什。如果中国政府没有把我赶出国的话,我在兰州,我的户口在那里,我到兰州来,我在兰州又待不下去,因为我有犯罪记录,最终我就没办法待了,跟家里一块儿去土耳其。
到土耳其以后,安卡拉的中国大使馆把我的护照取消了,当时我有八个月的有效期,他把我的护照取消了,然后我就成了无国籍人员,他让我回家,回去,三个月之内我必须回去。我以无国籍身份在土耳其待了四年,然后当时我申请一个国际作家庇护项目,那个项目支持我,请我到挪威来,去卑尔根这个城市。
现在在做什么呢,我还是从事语言保护工作,比如说我在给维吾尔族孩子写书,我到现在写了15本书。然后我出版了教科书,text book, 六册,从一年级到六年级。还在写,我给小孩写书,是我的一个爱好,是一个自我修复,自我修行,自我治疗的一种方式。因为这个 human rights,人权,这个事情,就是你总是听到不快乐的事情,总是听到有人被抓了,有人被判了,有人被打死了,有人枪杀了,就那种,每天听到就那种事情,所以给孩子写书,就帮助我远离残酷的现实,感觉很好。所以我一边给孩子写书,一边教孩子维吾尔语。
我在网上教维吾尔语,一边给老师讲课,培训他们怎么样教语言,怎么样教维吾尔语,怎么样教 heritage language, it means the language you can listen to it, but you can’t speak. This is the language we call the heritage language(这是一种儿童能听懂但是不会说的语言)。到不同的学术研讨会,探讨我自己学到的研究成果。
低音:作为一名语言学家,尤其是致力于保护维吾尔语言的语言学家,Abduweli 非常清楚维吾尔语的历史。在接下来的分享中,他梳理了从晚清以来,中国不同政权统治时期,维吾尔语言所经历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他的讲述中看到,维吾尔语是如何一步一步在中国被“消失”的。
Abduweli:很多语言落到弱势地位,(是)教育的原因,比如说在西方殖民者到印度,现在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类,到那个地方之前,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有些语言在印度也消失。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那些语言没有更新,没有办现代教育,他们要受现代教育的话必须去英文学校。中国有五四运动,洋务运动,就办了现代教育,日本也办了现代教育,韩国也办了现代教育,所以有了现代的文学,现代的思想都有。
维吾尔语也有这么一个更新的年代,1886年在喀什附近的一个乡办了现代式的学校,就是新式学校,可以说维吾尔语到现代的阶段,是1886年那个时候,办了新式教育,然后有了维吾尔语的中学,然后大学。1928年有了第一所大学,新疆大学的前身是1924年成立的。喀什是1934年有了第一个师范学校。维吾尔语到了这种现代(化)的阶段,然后现代教育要求现代的文学,有了现代的文学,现代技术科学方面的词汇,然后更新了自己。所以维吾尔语的发展跟时代有紧密的联系。
中共到维吾尔家园之前,(当地)已经有了完整的教育体系,这个对维吾尔语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20世纪初有了蓬勃发展的教育体系,在喀什有了现代的出版,印刷厂和出版社。喀什的出版社是1909年,喀什有了印刷厂。1919年办了第一份报纸,第一份报纸在喀什和伊犁,现代意义的报纸。1921年有了一个现代意义的出版社,是瑞士的传教士带到喀什,他们在喀什也办了个中学。现在的维吾尔语有好多英语词汇,就是通过瑞士的传教士他们办的学校,他们办教会医院,通过那些渠道学到的。维吾尔语那段时间,蓬勃发展的阶段,尤其是在喀什。1933年,喀什被解放,然后当时在喀什成立了一个共和国,East Turkistan Islanmic Republic,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那个共和国四个月以后就灭亡,但是喀什的那种觉醒延长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的老家乌帕尔乡有过两个剧院,一个在乌帕尔乡中心,另外一个在离乌帕尔十公里以外的一个地方。我2002年去过,我就特别惊讶,就说人家1933年建了这么大的剧院,一个乡里头,那个乡有3万人,3万人的乡有两个剧院。我就那个时候很佩服,人做了那么好的事情。所以语言的发展跟教育有关系。还有你必须有文学,你必须有话剧。我小时候在喀什有很多电影院、剧院,1933年到1937年四年里头,喀什有了很大的发展。
共产党来了以后,1949年到1957年,还是很不错的。限制是有的,镇压是有的,但不是很大面积的。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还是第二个共和国的,1944年在伊犁建立的第二共和国,他们生存了六年,他们有了大学,培养了好多知识分子。但是1957年以后就不一样了,1957年以后,在中国开始了“反右”,反地方民族主义的一个行动。保护传统的那些人不是维吾尔族,地方民族主义、民族分裂就是维吾尔族。
在(90年代的)中国,镇压法轮功的话,在北京他们镇压就是法轮功,但是新疆,他们不镇压法轮功,就是镇压维吾尔族的宗教人士,因为新疆没有法轮功嘛,当时名字就是法轮功,但是针对的、镇压的就是宗教人士。到新疆来,就是“反右”,右就是维吾尔族了。一大堆汉族的红卫兵拆庙,北京人很愤怒。但是新疆就不一样了,一大堆汉族红卫兵拆维吾尔族的清真寺,这理解方式不一样,他们觉得这是汉族拆我们的清真寺。同样的一个事情,在北京发生和乌鲁木齐发生,是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北京人拆北京,那是自己的事情,但是北京人到新疆拆我们的清真寺,那是汉族人,汉族殖民者破坏维吾尔族(文化),这么一个理解方式。
不光是共产党,冯友兰,中国的一个哲学家,他说过什么,西北是文明没有达到的地方,冯友兰不是共产党员。那种殖民的心态,唐玄奘也有。《大唐西域记》最后一章,就说他们不说人话,西域的人不说人话,这种心态,不光是共产党的问题。这种心态也迫使维吾尔族、维吾尔语在劣势的状态,不光是共产党。
对,共产党做了好多坏事,坏事就是1954年,把我们一千年用的那种文字体系都取消了,研制了一个新的文字体系。我们成千上万的人一下子成了文盲,1954年。1964年,10年以后,又改了,改成什么,改成一个新文字,新文字就是拉丁文字母嘛,拼音嘛,通过拼音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字。62年到82年,用了20年,然后是什么,又改。82年,改另外一种样子。从共产党统治新疆,54年一次,62年一次,82年一次,频繁的换这种文字,那你的语言怎么发展?那你写的书,你的弟弟看不懂,你弟弟看的懂的时候,你孩子看不懂,就这么个事情,所以这也是成了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从沿海开始的,所以思想解放也是沿海开始的,在沿海地区出版了很多书,很多语言材料已经有了,吸引你的,好多好多东西都有,但是维吾尔语,因为没有思想解放,因为没有改革开放,所以维吾尔语有好多好多书都没写下来。原因是什么?没有市场经济,你就重复陈词乱调,就是50年代那些东西,你还在写,但是北京已经变了,上海已经变了,乌鲁木齐还是那个乌鲁木齐,喀什还是那个喀什。
我1992年到北京,我就觉得北京给我感觉就是一个美国,因为那个时候在北京虽然有八九运动,但是我去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生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杂志,有自己的文学论坛,但是民大,同样一个北京,没有学生论坛,那维吾尔语族学生上学的一个系,当时是民族语言二系,我们办报纸的权利都没有。而在喀什,在乌鲁木齐呢,他们办报纸的想法都没有。那个时候在北京已经有了盗版的书,新疆盗版概念也没有。维吾尔的书都是那些什么,毛泽东选集乱七八糟的东西,谁看?盗版版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是2000年以后出来的。所以维吾尔语的发展很慢,原因是改革开放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呀,到新疆改革开放是1996年的时期,所以这个也妨碍了维吾尔语的发展。
中国的出版社都承包了,但是新疆的出版社、电视台和报纸,一个都没有承包。私人出版社那是根本没有的事情。我在北京的时候,有私人出版商,在新疆没有私人出版,私人的书店都没有。在维吾尔地区私人书店,第一个是我们开的,是1995年开的。1995年才有了第一个私人书店。(之前)没有私人书店,没有私人出版社。没有出版自由,没有新闻自由的话,这个语言怎么发展?
当时我就94、95年的时候就写过一篇文章,《维吾尔语是维吾尔族的一个监狱》。为什么我写那篇文章?因为维吾尔语有的东西都是那些50年代的东西,跟时代没有关系。要获得自由的话,要学习汉语,然后获得自由,然后你(能)学到在世界发生什么。看世界通过维吾尔语看,维吾尔语的那些词汇,那些表达方式,都是50年代、60年代的那些东西。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变了,但是维吾尔族没变。
我在北京看过"1984”,“Animal Farm”,我在哪个书店买的,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建国门外那边有一个书店,我去那买的。1984是什么时候翻译成维吾尔语?2014年。你没办法翻译成维吾尔语,因为当地政府不允许。翻译了以后,一个就是没有市场化,比如说那私人翻译,没有人买。
低音: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现在的维吾尔地区是什么样子呢?街道上仍然可以看见维吾尔语的标识吗?广播和电视里听到的是什么语言?维吾尔的孩子在哪里接受自己的母语教育?在接下来的部分,Abuduweli 给我们描述当前中国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和那些被迫适应汉语的残酷现实。
Abduweli:现在的比如说报纸电视还是有维吾尔语,但是都是汉语的翻译,就是政治那些东西。其实是有,维吾尔语的广播有,维吾尔语的报纸有,不像以前那样多,现在少了。以前在当地的电视台都是维吾尔语,比如说喀什有喀什电视台的维吾尔语版,阿克苏有阿克苏电视台的维吾尔语版,但是现在这个取消了,当地的那种维吾尔语版的电视节目都取消了。但是新疆电视台的维吾尔语版还是有。《新疆日报》的维吾尔语版还是有。新疆主要的那个文学杂志还在出版。
1986年,有些维吾尔族的学者从国外回来,不是1949年有好多维吾尔族跑到国外去了吗,跑到土耳其,跑到沙特阿拉伯,跑到俄国那些,有一部分人回来了,1983年,1986年那段时间回来了,带来了一些好的东西,比如说文学方面,思想方面的。他们的思想没有找到市场,也没有找到空间,但是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一个人就受到西方的影响,办了一个杂志,通过乌鲁木齐文联的允许,那个杂志叫《天尔塔格》维吾尔版的,天尔塔格是天山。这个杂志2017年在这个大抓捕、种族灭绝以后就改成《天山》,内容都成了汉语文学的翻译版,维吾尔文学比如说诗歌那些东西,都是歌颂党的,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2017年以后,全部学校的老师换掉了,维吾尔老师都赶回家,都从内地请来了汉族的老师,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全部成了汉语。最近采访20多个维吾尔族,从新疆不同的地区来的,他们说现在13岁以下的孩子都不说维吾尔语。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新疆不是分给18个省份了吗,18个省份过去那些老师用的方言都不一样。从上海过去的幼儿园老师说上海话,从广东过去的老师讲广东话,然后他们两个互相听不懂,现在成了这种现象。我朋友说现在最麻烦的事情是这个,虽然他们都说的是汉语,但是上海的老师和福建的老师讲的汉语,跟甘肃过去的老师(不一样)。小孩都听不懂,因为他们从小跟那些老师,模仿他们说话。
最残酷的是寄宿幼儿园,寄宿学校,是很头疼的事情,是失去语言文化的一个坟墓。但是寄宿幼儿园是更严重,因为寄宿幼儿园就是他们在那住、吃,所有东西都在那里,跟家里没有联系,被迫的,然后有的是一个星期回一次家,有的一个月回一次家。这个寄宿幼儿园是最头疼的,最让我痛心的事情。我现在在写一个报告,有关寄宿幼儿园的。我希望这个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政府最起码把孩子还是(让他们)在家里住。
低音:多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在汉人和维吾尔人之间的怨恨和不理解越来越深重,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些仇恨和怨恨?在汉字和普通话作为“日常”和“正常”的所谓现实当中,我们怎样去理解,抹去一个民族自己的语言是一件残酷和践踏人权的事情。为什么像 Abduweli 这样的人仍然在努力地保护维吾尔的语言和文化,尽管越来越难。
Abduweli:如果我们失去了维吾尔语的话,就我们这个维吾尔族,有一千五百多年的文字记载,成千上万的书都没人读,就是就很可惜。你不能让一千五百万人失去交流的工具,科学研究的,文学创造的工具。语言不光是一个交流的工具,那是基本的人权。比如说广州人有权利使用 Cantonese,那维吾尔族就是作为一个个人也罢,一个民族也罢,有权利用自己的语言,这是不可夺走的一个权利。我们这个世界充满冲突,怨恨,原因是我们的人格,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情感,没有得到应得的尊重。这个很残酷的现实。
在乌鲁木齐长大的一个维吾尔族和一个汉族孩子,ta们是无辜的,但是一个在寄宿幼儿园,从三岁开始离开了自己的父母,离开自己的文化,另外一个是汉族孩子,ta早晨跟爸妈一块高高兴兴的出门,晚上高高兴兴的回来,说自己的故事。将来,这两个孩子,ta们会说同样的语言,但是失去父母、失去文化的那个孩子,会永远恨那个(汉族)孩子。有了你,我失去了我的父母,我失去了我的文化,原因是有了你。实际上是这样子吗?没有,那个(汉语)孩子没有罪,但是很难解释清楚。说同样的语言,没有同样的感受,那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很难。
Ta永远记得自己被强迫在幼儿园里头,这个怎么解释?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在一个集中的学校里头,ta没有活泼的权利,ta不能享受自己的童年,怎么可能ta们以后能活到一块?那这个是谁造成的?我们应该想到这一点。那失去语言的,失去自尊的,失去骄傲的那些人,永远恨对方。这个怨恨,这怎么造成的呀?我们为什么有这么个东西?那互相残杀,争夺什么?新疆很大,我们不应该争夺,那么大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活,都可以活,那为什么强迫对方跟我们说一样的语言?为什么?我们可以使用同一个语言,但是你不能把我的孩子偷走。你不能把我的童年偷走。你不能把我的父母偷走。你不能把我的文化偷走。你不能殖民我的文化,殖民我的语言,殖民我的家乡,这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要尊重,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