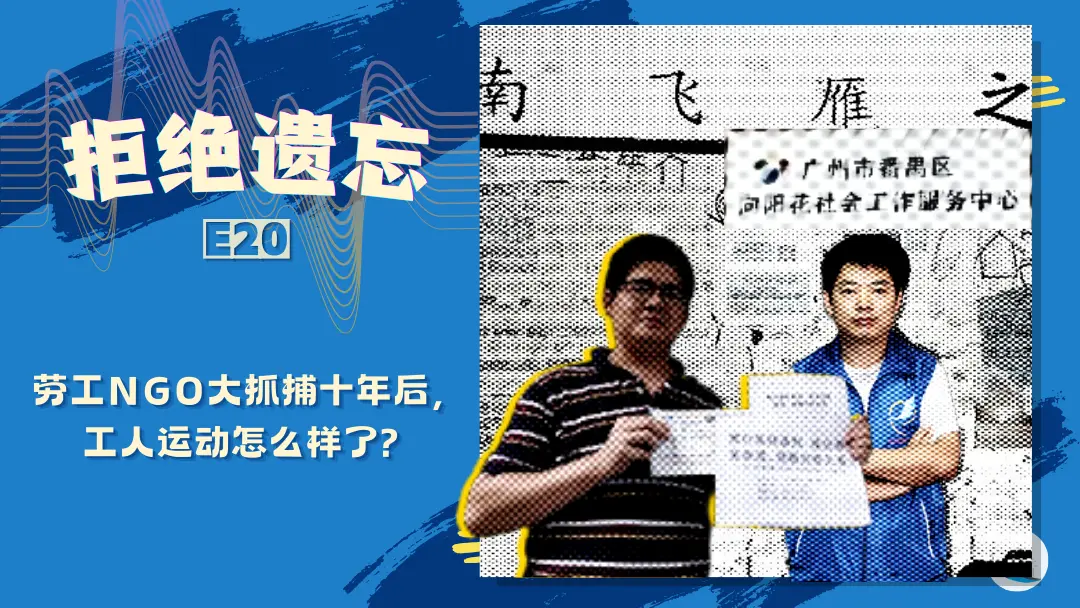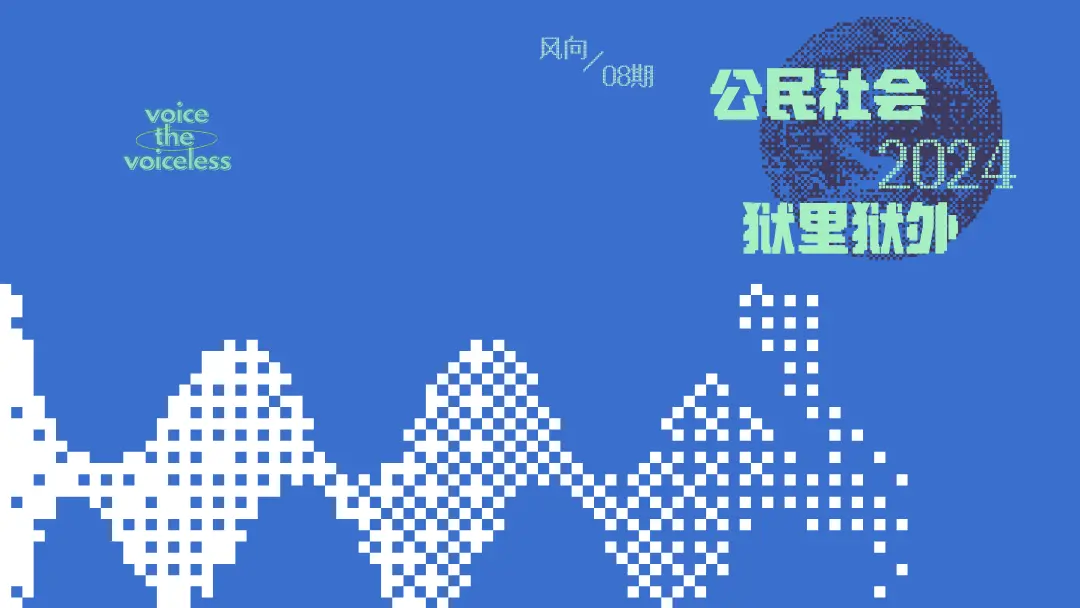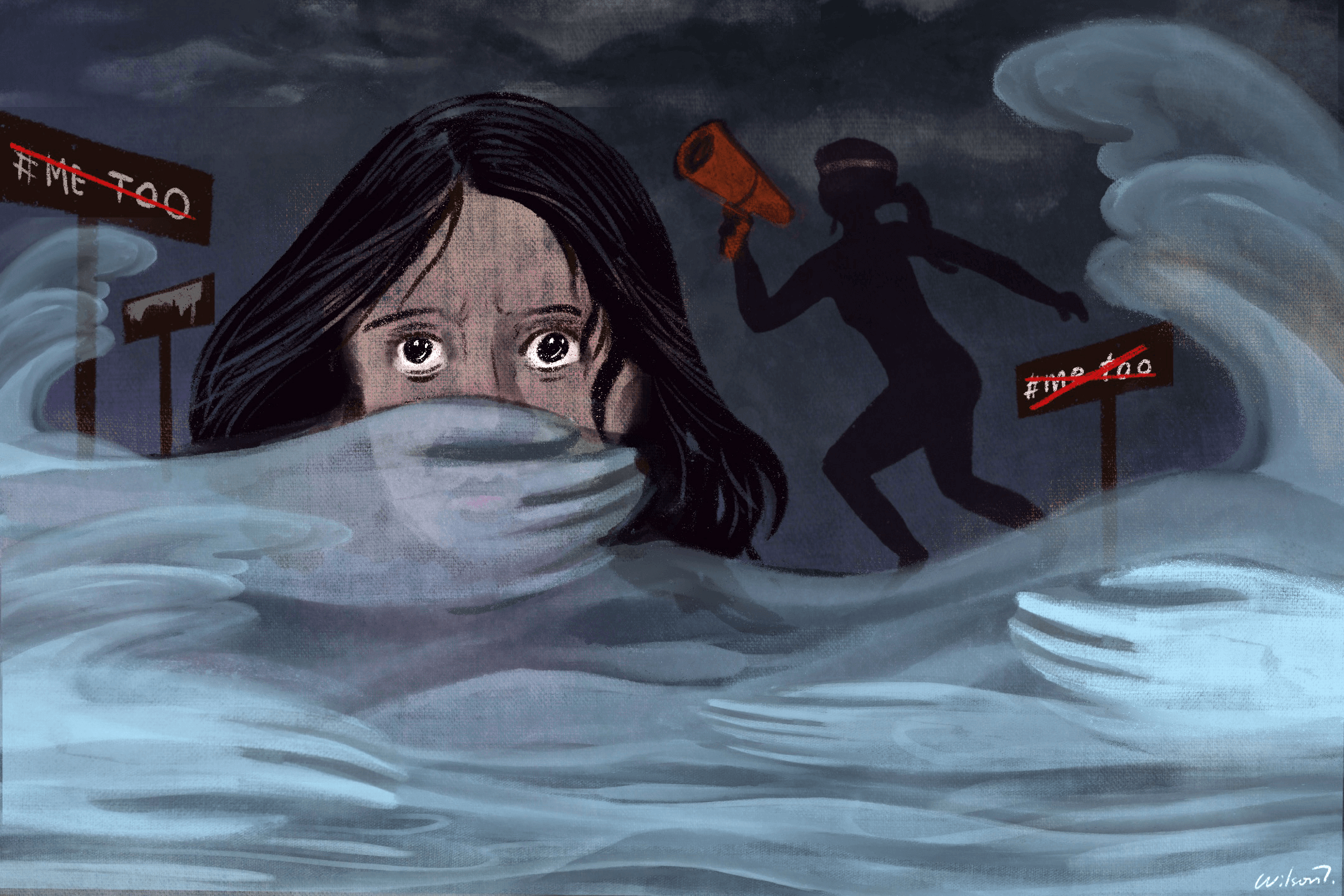- 口述:Ellen David Friedman
- 整理:瑞德
点击阅读本系列的上篇。
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我第一次访问中山大学的时候,去见了社会工作项目的老师和一些研究生。他们为我安排了住宿 ,让我去听一些课,和大家进行一些讨论。有一次晚饭或会议结束后,一个研究生送我回招待所,因为校园很大,我不熟悉那里,他们认为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回去的路。他问我,是否认为NGO有可能在中国发展起来?他的问题非常真诚。他对NGO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但他显然非常怀疑它们是否能在中国发展起来。因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所认为的“公民社会”的概念,是在过去几百年里发展起来的,它不是一个普世的事实和存在。它反映了国家、被治理者、资本、工人等等之间一种特定的阶级、政治和经济关系。
我记得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当然,NGO当然可以在中国发展。”但直到我住在中国,在十多年的时间不断往返于中国和美国之间,我才明白,这也许是可能的,但不该被假定是必然的。我的观点逐渐变为:中央政府很可能会容忍某种形式的公民社会发展,但我完全不知道它的限制在哪里,也不知道这些限制将在何时何地显现出来。
当我在中国时,任何看起来像公民社会中的空间开放都是令人惊奇、鼓舞人心的,对大家来说是一种令人振奋和兴奋的体验,对我来说也是如此。等我回到美国,变得清醒了一些,也有了一些更多的视角,在习近平上台前后,甚至可能在那之前,我就开始对人们说,我会把这看作是一扇正在打开的窗户,但这扇窗户随时都可能关闭,而且我觉得它终究会关闭。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他们对待最早的西方贸易商、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方式,一直以来都是维持着对边界的严格控制,不仅仅是地理边界,还有政治边界、经济边界、文化边界。当它做出开放的决定时才会开放,当做出关闭的决定时就会关闭。我经历了这扇窗户关闭的过程,而且这种关闭仍在继续。尽管如此,那段经历仍然是相当令人惊奇的。
我认为从致丽大火(低音注: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发生火灾,共造成87人死亡,51人受伤)开始,学者们开始密切关注中国的劳工议题。那场火灾夺走了许多年轻女工的生命,我知道这并非唯一事件,但它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件,尤其是在香港,学生、活动家和公民社会的参与者开始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生产和劳工制度重新分配的本质,在广东数千万农民工、数千家工厂的存在,以及那一时期所特有的过度剥削。因此,我们看到香港的许多工会、劳工NGO和公民社会NGO开始关注,开始来到广东进行研究。这似乎很自然地促成了对一些项目的支持,这些项目后来变成了劳工NGO,小型劳工中心。这些支持是非常公开的,并不是秘密进行的。据我所知,有国际基金会、西方基金会,通常是宗教或慈善的机构,比如“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或者乐施会(Oxfam),以及其他一些机构,它们向香港的组织提供资金,这些资金随后被用来建立那些中心。
这些中心具有多种多样的性质。有些是文化性质的,工人们会被邀请来做饭、唱歌、读诗、只是娱乐放松,有些建立了小型图书馆,有些放映电影,有些会走出去,在工地上与建筑工人见面。一些中心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健康与安全问题,并做了大量工作来帮助工人了解如何为工伤或职业病获得补偿。还有一些中心,特别是在 2007 年和 2008 年之后,随着劳动法律的制定,开始进行劳动权利教育,帮助工人理解集体谈判,工会如何运作,还有如何向雇主施压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些劳工NGO在全国范围内数量从来都不多,中国太大了,我认为全国最多也就 40 个。它们规模也很小,工作人员非常少。在我的观察中,它们不反政府,不反党,其中很多甚至不反(官方)工会。有许多人认为工会可以而且应该发挥作用,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尝试与当地工会官员接触。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现象,在一个快速工业化的社会中,这是一个恰当的发展。
与此同时,其他公民社会的发展也在并行发生。我最了解的当然是在广东,尤其是在广州、深圳及其周边地区的情况,但我也听说过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
有一家NGO,是我在广州遇到的第一批组织之一,它叫“家”,由一位日本年轻人创立,为那些居住在麻风病村(即麻风病患者村庄)的年事已高的居民提供非常基础的服务。这个年轻人非常有魅力,会带学生到这些村庄去做一些房屋修缮,或者修复基础设施。
社会工作、公共服务方面,有很多努力和兴趣。那时候学生们喜欢到更偏远的农村省份,花一些时间在乡村学校支教,或者组织一些夏令营活动。
还有律师,有一些公共服务律师、公益律师,他们成立了一些我们称之为公益律师事务所的小机构,其中有些是商业性的,有些是非营利性的,但它们都属于公民社会领域。
媒体一直是非常敏感和受限的,所以独立的公民社会活动不太容易在媒体上展现出来,但它仍然做到了,一直都有各种网站、微信群,以及各种媒体方式。
LGBTQ 群体开始出现聚集和组织,尽管这仍然非常敏感;显然,女权主义者也在组织起来。当时有一些精彩、极富创意又幽默,几乎像街头戏剧一样的表演。其中有一个是为了展示企业招聘中对男性和女性申请者的区别对待。她们提交了所有细节都完全相同的求职申请,但一个是男性的,一个是女性的。结果,针对女性的拒信堆积如山,而男性申请者都被接受了。我记得有一天,年轻的女权主义者骑着自行车穿过城市的某个区域,带着那一大堆拒信。
还有婚纱上溅着血迹的行为艺术,以及在公共厕所排队,以表达公共厕所的分配方式应该有所不同,女性应该比男性拥有更多数量的隔间。所有这些事情都让人感觉如此新颖,它们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这就是为什么我用了“爆炸性”这个词。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关于乡镇和村级选举的倡议,这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事件。我不记得是哪一年了,但它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一些土地改革新举措有关。土地永久归国家所有,但农民有什么权利,土地可以出租多长时间、租给谁,这些问题一直在持续。我记得当时正在进行一些相当重大的变革,我不确定是全国性的还是只在广东,而且它也存在争议(低音注: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政府开始探索农村土地流转和经营的新方式,与此同时,土地财政滋生的腐败,也激化了农民和政府的矛盾。2011年,广东汕尾市乌坎村村民因不满村干部私自卖地,爆发示威抗议,最终由村民一人一票的形式直选出新村委会)。
与此同时,还宣布了某种程度上开放乡镇和村级领导选举权的政策。这种形式的选举也来到了广州,我记得有一些学生宣布他们将要参与一些较低级别的、区级选举或其他什么(级别的选举)。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低音注:2000年开始,中国出现了独立候选人参选基层人大代表的现象,2011年当年,全国共有数百位独立参选人,成功案例不多,包括司马南于2003年当选北京东城区人大代表,许志永于2003年和2006年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我记得当时我在关注这件事,并和其中一些人交谈,心想:“好吧,我们拭目以待。” 我不认为它会走得很远,当然它确实没有走得很远。但那些就是当时一直在发生的事情,太令人惊奇了。
那段时间太棒了!太精彩了!我忙得不可开交。那十年我工作得非常努力。(我的生活)经常是这样:艾伦,这份报告你肯定会感兴趣,是关于学生们寒假期间去富士康工厂工作的,来听听这个报告怎么说;这里有部电影,或者有一位外国劳工学者来访,来自德国、巴基斯坦什么的,我们应该来见见。 总是有学生来找我,他们很好奇,而且通常他们很害羞,但他们想更多地了解我们正在讨论的内容,所以我经常会预留时间和学生们一起吃午饭,或者约人吃晚饭。
我真的非常忙。我记得有时我确实没怎么睡。有一点是,我教书的时候有很多挑战,因为班级非常大。典型的班级有 60 名学生。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不知道大多数学生可能会怎么想,或者他们能学到什么。所有课程都是用英语授课的,这对许多学生来说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有时一些学生会为我翻译。但无论如何,我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我每学期会教很多课,两节或三节或四节课。而且我会组织独立的阅读小组。
每节课都有 PPT,有阅读作业,有活动。我从不只是讲课,这不是我的做法,我不认为人们是通过那种方式学习的。所以我总是在努力想办法让大家参与进来。这相当有挑战性,因为大多数中国学生习惯于讲座模式。我找到了方法。我布置了阅读作业,布置了写作作业,因为我想,他们可能不想在课堂上发言,但他们会写点东西。然后我就有了几百份写作作业。我很认真地对待,我全部都读了。我给他们打了分并做了批注。
当然,对我来说,在一个学期里记住学生的名字也是极具挑战性的。我希望记住他们的名字。我记住了一些,但不是全部。我不想用他们的英文名字,我觉得那不尊重。所以我会让他们告诉我他们的中文名字,我可以练习。
我非常努力做所有这些事情,但这太疯狂了,那是如此多的工作。我确实很喜欢,从中也学到了很多,正因为我花了所有这些时间,并如此认真地工作,我回到美国后才成为了一名更好的老师、劳工教育者和组织者。
和工会官员的合作与友谊
我与广东省总工会、广州市以及一些区级的工会组织进行了大量合作。
当时广州市总工会的主席是一位非常敬业、非常正直的人,我非常了解、信任并真正钦佩他,也非常喜欢他。他名叫陈伟光,是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人。他在广州出生和长大,和我同龄。我还在中国的时候,他仍在任上。
他对许多事情都非常开放,这让我们很惊讶。他参加了我们的会议。他来到大学给学生们演讲。他允许我们组织的外国劳工学者、外国工会领袖的访问。我们也邀请他去美国做劳工考察,他带领一个广州市总工会领导的代表团访问了美国。
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非常深厚和重要的友谊。我们都从彼此身上认出,对方是真正致力于工人阶级和工会主义理念的人。很多人质疑我为什么会不断回到中国,是有人付钱给我吗?我是在执行秘密任务吗?他们能信任我吗?我理解这一点,因为我做的事情很不寻常。我不完全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但我就是停不下来。
我认为陈伟光相信我是值得信任的,我来这里不是为了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我不是境外势力,我没有秘密计划。我认为在中国最好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坦诚,我做到了,而且他也逐渐开始信任我。这花了一段时间。
他非常谨慎,每当我提出建议:“你觉得这个怎么样?这是个好主意吗?这可能吗?”他总是会非常认真地对待,对我的想法表现出极大的尊重,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提出的所有建议都可能实现。但我非常信任他,他知道什么是可能的。如果某件事可能,他会说“是”;如果不可能,他会说“不”,然后我必须信他的话。
例如,他邀请我在广州市总工会的年会上发言。他告诉我,这是自工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有外国人被邀请发言,甚至只是出席,不仅是发言,而是出席。所以我想他信任我。当然,我必须事先把我的发言稿交给他们,他们必须翻译,但显然他们不会让我随心所欲地说任何我想说的话,我非常尊重(这一点)。我讲了一点我在中国看到的情况,但主要是利用这个机会谈论美国的劳工运动,以及我们劳工运动之间合作的潜力。
还有当时的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名叫孔祥鸿。他对一些改革也有兴趣。在我看来,他远没有陈主席那么进步,尽管如此,他处于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职位,而且他很慷慨,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感兴趣。
后来,我邀请陈伟光来我们的公寓吃晚饭,由我丈夫做饭。我丈夫很擅长做中餐。陈伟光花了很长时间才同意,肯定有几周,也许更久。
他来的时候,带了其他几个人。其中一位是担任他口译的女士。她被分配负责国际关系,是一个年轻女性,英语很好,而且很专业。我从来不觉得她真正认同陈主席和我的观点,但我认为她很可靠,而且陈主席是她的上司,所以她来了。
我很确定另一个人也来了,我和他之间关系有点有趣。他显然是党的人,我不知道他的头衔是什么,但他似乎是一个在工会里党的官员,他肯定是为了来监视(我们),我们都知道,我们从不谈论这件事,但我们都明白。
然后是我的丈夫斯图尔特,还有我自己,我们的儿子伊莱当时在中国做研究,他也来了。
我们都非常紧张,我记得我们住在校园里一间很小的公寓里,就在中山大学校区大西门旁边,那是教职工宿舍区。我们是从一位那个学期不在的教职员工那里租的公寓。斯图尔特花了很多时间做饭,我花了很多时间打扫。
那是一顿美妙的晚餐,我记下了很多笔记。我坐下来,把陈主席说的每一句话都写了下来。他非常放松。我认为那是一个转折点。他后来告诉我,在那晚之前,他从未在外国人家里吃过饭,我真的很感激他足够信任我。
我很有雄心壮志,想尽可能高效地利用我在那里的时间,所以我问了很多事情,比如我能去工会总部吗?我能与区级或社区级的工会官员见面吗?我能为我的学生组织研究项目吗?是什么样的研究项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做?他能来我的课堂上演讲吗?伊莱也问他是否可以帮助他安排一些研究访问,去各种地方。
我们不断地问很多事情。我就开始等待那个特殊的词——“可以”。一次又一次,我总是在等待它。
我知道他想提供帮助,但我也知道他能做的事情有很多限制。巨大的限制。我确信我从未完全理解他所面临的所有限制。仅仅因为和我建立关系,他有没有承担后果?也许有。如果有些人对此非常怀疑,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后来我也邀请陈主席来美国进行劳工考察。肯定有一次,也许两次。那位党的人也参加了其中一次或两次。我组织劳工考察的风格是把每一分钟都排满,安排会议、讨论和参观,一点旅游都没有,有时我甚至忘了安排吃饭时间,所以我不得不经常和那位先生协商。陈主席告诉我,我需要和那位先生协商,我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方式来。
有一天晚上,我们应该是在拉斯维加斯,因为我记得我带他们去了HRE工会总部开会,那是酒店餐饮员工工会,代表那些赌场工人。那位先生宣布,他负责那一晚的活动。我说好吧,因为陈主席告诉我必须让他来做。他安排了在赌场吃晚餐,我不记得所有细节了,但最终我们去了某个地方看表演。结果那是一场脱衣舞表演,我本人完完全全感到被冒犯了,但我不能抗议。
我坐在陈主席旁边。表演内容一明确,他就拿了一把扇子或一本书或什么东西,盖住了自己的脸,把头靠回去睡着了,或者假装睡着了。我觉得那太棒了,太聪明了,我感觉“哦,好吧,他也讨厌这个。” 是的,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瞬间,那是一个美好的瞬间。
未完,请继续关注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