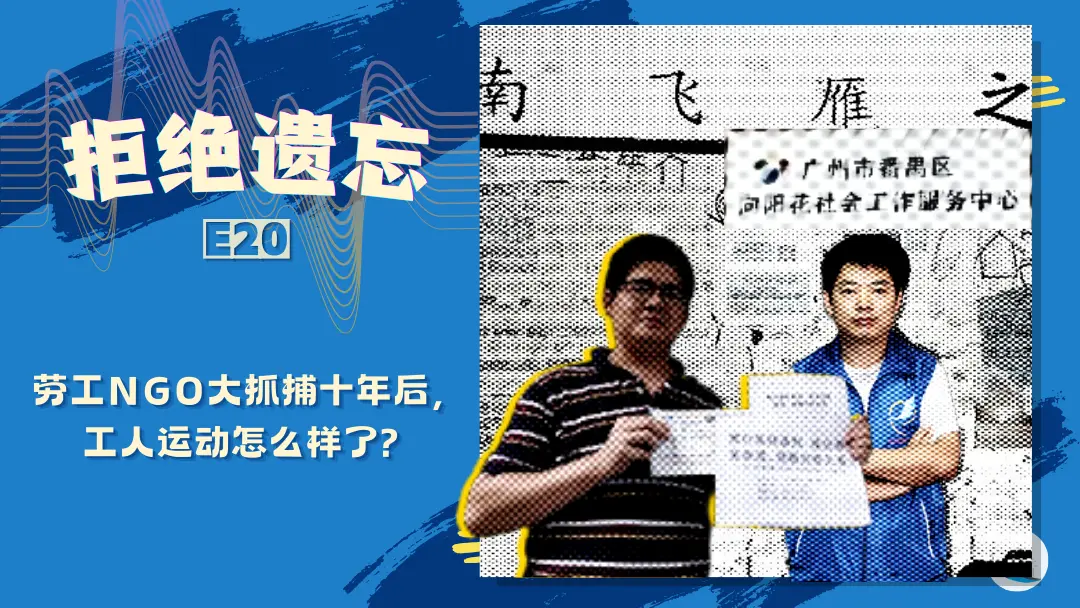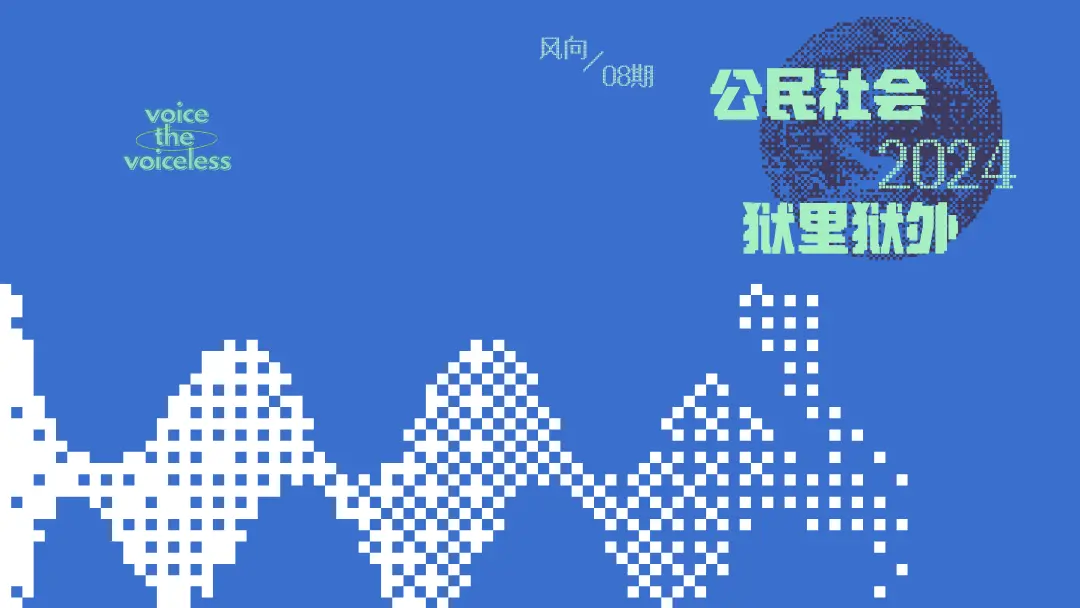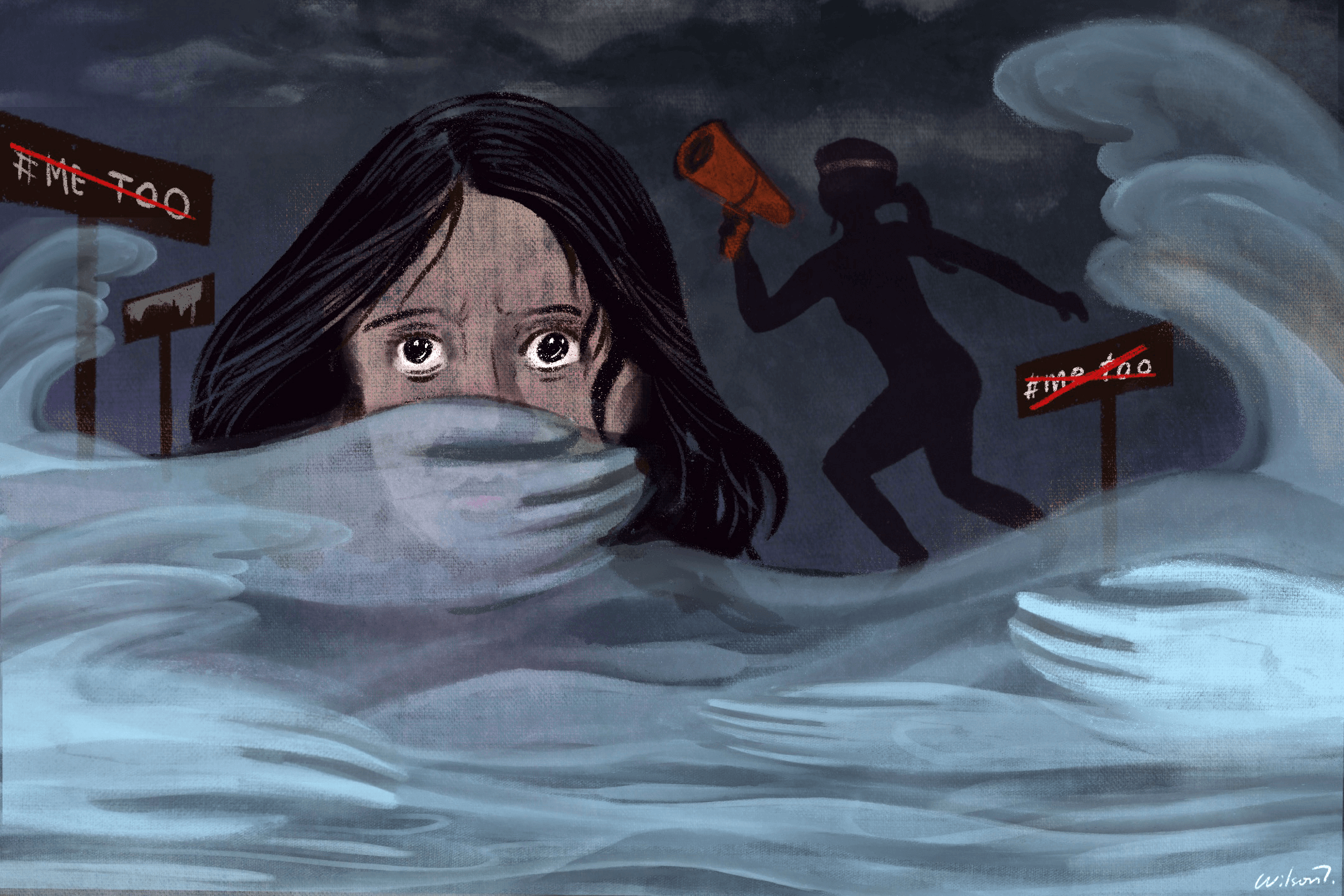- 口述:Ellen David Friedman
- 整理:瑞德
2015年12月初,广东多地警方突袭劳工机构,逮捕了多位机构负责人、志愿者等。这场大抓捕和3月的“女权五姐妹”,7月的“709律师大抓捕”一起,标志着2015年成为中国公民社会走向寒冬的转折点。
在这场抓捕过去十年后,美国劳工组织者Ellen David Friedman向低音回忆了她所经历的2015年,中国公民社会和劳工NGO的发展和衰落。她曾经在中山大学执教,在广州工作生活了约十年。
2015
是在2015年12月,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我先在香港,然后去广州。香港比我预想的要冷。我记得当时我在两个会议的间隙,冲到一个有许多夹克的市场摊位,用最快速度抓了一件,把一些钱扔给摊贩,我当时非常冷。那次旅行中我一直穿着它,而且从那以后,每到冬天我都会一直穿它。它现在依然很耐穿。它是一件非常鲜艳的黄色冬季短夹克。
我去广州当然是为了看望学生、朋友和同事,因为到那时为止,我已经在广州工作了大约十年,积累了一大批朋友和同事。当时的计划是,第二天会有一些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学者到达,和我以及我的儿子伊莱一起开会,他是一位研究中国劳工的社会学家。我们计划在会议上讨论一些关于教师劳动条件的研究,这是我一个长期的兴趣点。
我当时住在中山大学校区附近的一家酒店。那天下午,我听见有人敲门,一个非常紧张的女人站在门口,她看起来像是酒店保洁,说了一句类似“我来打扫您的房间”的话。但我知道她不是(来打扫房间)。站在她身后的是一大群人。一分钟之内,她就离开了,他们所有人都进了房间。
我记得有一个男性负责人提问,他对我讲中文,有人把他的问题和评论翻译成英语,还有另一个人把我的回答翻译成中文。我的中文非常差,所以双向都需要翻译。可能还有两个人守在酒店房间的门口。总共是五个人。负责的男子长得不错,大概快四十岁,也许四十出头,中等身高,中等身材。翻译人员是一男一女。我不记得谁是翻译成英语,谁是翻译成中文的。那两个像警卫一样的人都是男的。
询问大约两个小时,他们相当有礼貌,没有搜查我的行李 。只有一两次,他们不喜欢我的回答,而且有点强硬。负责人有一次说:“你违反了你的签证规定。”我回答说:“我现在的所作所为和过去没有任何不同,我已经来了十年了。我怎么会知道呢?”我抗议说:“从来没有人说过我的行为违反了我的签证规定。”他说“这是我们的签证,由我们来决定”,这倒是事实。
他们显然对我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们会问:“你都见了谁?”我说:“我的朋友、我的学生和我的同事。”他们想知道人名。我说:“不,我不会告诉你们任何人的名字。”但后来他们会具体地问:“你为什么要见这个人或那个人?”所以他们非常清楚。我并不感到惊讶,我想他们已经获取了我的电子邮件通讯和电话记录。
很有趣的是,他们问我为什么在课上教某些书。我记得有一本书,他们问了很多。这本书叫《韩国工人》(Korean Worker: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是关于 1980 年代纺织工人故事的。这本书是重要的劳工历史文献,所有研究劳工的学生都对它非常感兴趣。他们知道我在教这本书,问我为什么,我说:“这就是劳工研究的内容,我们研究劳工。”他们又问:“为什么中国学生会对韩国的劳工运动感兴趣?”我说:“那得问他们了。”总之,他们对我以及我所做的一切都非常清楚。
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点,我是否把外面的钱带进中国。我说,没有。实际上,我不可能花任何钱——我不是指房租或吃饭——每个人都非常清楚,对于我们通过在中山大学成立的劳工中心所做的任何项目,我不能带入外部资金,这有非常严格的禁令。我说,我用少量资金请一些研究生为我做口译。一直都有人为我口译,当然他们都非常慷慨,但有时,比如我要去参加一个会议,需要六个小时的口译工作,那是大量的工作,我会提出支付他们一些费用,帮他们买火车票,或者请他们吃饭之类的。
我回美国的航班是在下周初,可能就在会议结束后紧接着的那个周一或周二。他们显然知道我的航班是什么时候,最后说:“按时搭乘那趟航班。”他们并没有说我必须提前离开,但我必须按计划离开。
他们告诉我,不要跟任何人说发生了这件事,就待在这里,不要和任何人说话,然后直接去机场。但我没有打算完全照他们说的去做。
他们离开后,我跟美国驻广州领事馆通了话,领事馆的人说:“你知道,他们有权这样做,他们有权讯问你。但我们也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三个小时内没有收到你的消息,我们会尝试查清楚发生了什么。”
然后我说:“如果你们联系不到我,或者很难查清楚情况,我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是多年的老朋友。他是美国参议员,他非常清楚我经常去中国。他知道我是劳工组织者。我每次去之前都会打电话给他的办公室主任,让他知道我要回中国了,以防万一。如果你们需要任何政治协助,他会提供帮助的。”
我其实并没有那么担心。我心想,我没有那么重要。我没有携带资金。我的目的与政府毫无关系。我不是反政府的。我在这里是为了了解工人,交流其他国家的劳工运动经验,并尽可能支持劳工研究、支持工人组织。但我确实给一些朋友和我的儿子发了信息。
我的儿子那天或前一天刚刚抵达中国。我想他当时在深圳,那天晚上就要来广州。他本来打算在酒店和我一起住,然后我们第二天要开会。我打电话给他时,他说他从我们的一些朋友那里得到建议,也许他不应该来看我,因为我肯定会被监视。我想朋友们警告过他,如果他现在离我太近,鉴于警察已经来过这里,他可能也会被监视得更严密,如果他想回来继续在中国做他的研究,这可能会很困难,会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我说:“但我是你妈妈,我刚才被警察讯问了好几个小时,所以我真的认为你应该来,这对我会有帮助。”他想了想,还是来了。
在我等他的时候,我联系了其中一个学生,他们通知了其他人。他们说:“我们在酒店大堂等你。”我说:“我不希望你们这样做,因为我不希望你们暴露在警察面前。”
总之,过了几个小时,我平静了下来。我本来应该在附近的一家餐厅和一些朋友吃晚饭。那是一家普通的餐厅,在大学附近,可能靠近中山大学的南门。它不是那种小小的面馆,是一家正式的餐厅,有桌子,有服务员,但不是很豪华。那是我最喜欢的餐厅之一,而且我要见的人,我记得这好像是我这次来中国最后一次见到他们了。这算是一次告别晚餐。那天晚上可能吃了饺子或者东北菜,我记不清了。
我走到大堂,看到有几个我的学生。我说:“我告诉过你们,我不认为你们应该在这里。”但他们说:“不,我们担心你,我们想留下来。”所以我跟他们聊了聊,让他们看到我没事。
然后我去了那家餐厅。在餐厅里,我本来要见的人正坐在房间的对面。我看到了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我走过去(对他们示意),说:“我不会过去和你们坐在一起。”然后我独自坐了下来,我们互相看着彼此。最后,他们终于走过来,和我坐在一起,说:“我们并不害怕。我们更担心你。”
第二天,我也见了一些其他的人。我发现,在我被讯问的同时,他们也讯问了其他认识我的人。虽然他们对我很有礼貌,对我的同事们却很不客气,相当咄咄逼人。听到这个,我非常不高兴。
我的朋友、同事们都听说了发生的事情,他们非常担心,想见我,想确保我一切安好。我的本能反应是不应该让我的朋友们暴露,因为我想我肯定会被跟踪,但是他们的态度似乎并不担心,都希望能继续我们的约定,我也照做了。那个周末我见了很多朋友和同事。
我很清楚,我回来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警告。警察告诉我,我的签证是旅游签证,如果我想回来看看中国许多美丽的景点,那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我回来做我一直在做的那些事情,是不能接受的。我对只是作为游客来中国毫无兴趣,所以我基本上认定,这将是我最后一次来中国。我想见我关心的人。我确实见到了那些我关心的人,然后就离开了。
我的离开过程没有遇到任何麻烦,没有发生任何异常的事情。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预料情况可能会更严重。但同时,我感到非常难过和担忧,担心我的一些好朋友和同事会因为我惹上麻烦。事实上,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甚至长达四五年之后,我都听到消息说,与我亲近的人会因为他们的活动受到讯问,他们有时会被问到我:“你认识艾伦吗?她是谁?她在中国做了什么?你和她有什么联系?”诸如此类的问题。
和中国的缘分
我们第一次去中国是去看我们的儿子伊莱,他当时上完或者快上完本科,开始学中文。有年夏天,他到青岛学习语言,我们在那里看望了他并进行了一些旅行。后来他回北京,在清华大学的一个项目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习,这是一个由清华大学和几所美国大学共同赞助的、历史非常悠久的语言项目。那个项目结束是非典流行的那一年。
去故宫和长城,这种游客式游览,我们确实去了。但我有着强烈的政治兴趣,而不仅仅是观光。我在大学时相当认真地学习了中国的现代政治历史,我对这方面很感兴趣,并且相对了解。我属于左翼立场,而且我几乎一辈子都是一名劳工组织者,是中国革命的拥护者。
我遇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你知道文化大革命期间创作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吗?它非常有名。我在1970年到1974年上大学,那几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是我真正研究中国政治事件的时候。而且我是一名舞者,我的大半青少年直到成年时光都在学习舞蹈。我对这部芭蕾舞剧印象深刻,看过它的电影,也阅读过相关资料,我觉得它非常棒。
我想是 2001 年或 2002 年的夏天,伊莱在青岛上学的时候,我和我丈夫去中国探望他。我们在上海市中心散步时,经过了一座大剧院,我记得有一个巨大的牌子在宣传即将上演的演出,主要的演出是一部名为《猫》的美国百老汇音乐剧,我觉得这很有趣,美国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视为资产阶级文化。但那晚唯一的一场演出是《白毛女》。我非常兴奋,我说我想去看。我丈夫和儿子不感兴趣,我就自己去了。
那是一个巨大的礼堂 ,坐得相当满,我猜想他们大多是老年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并没有那么久,大概是20 或 30年后,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经历了那些岁月,并与之有着某种直接的联系。
我坐在礼堂里,旁边是一对比我年长的夫妇。几乎从芭蕾舞剧开始的那一刻起,坐在我旁边的那位女士和我就都开始哭了。我非常激动。到演出结束时,我们几乎是手拉着手了。当然,我们无法交流,她不会说英语,我也不会说中文,但我们俩都非常感动。
我们第二次去中国,是伊莱在北京学习语言已经有几个月之后,他语言学习项目放寒假了,春节假期,那应该是在一月下旬、二月左右。那次很有趣,我们去了南京郊外的农村。伊莱认识了一个农民工,他就住在伊莱在北京公寓的地下室里。他们成了朋友。这个年轻人邀请我们所有人在春节期间去他家做客。
我们坐了火车,然后是公共汽车,然后是面包车,最后是摩托车,我们一整天都在路上奔波。我们去了非常偏远的农村。我完全不知道那是哪里。我们和他以及他的家人住在一起,我确信他们的村子里以前从未有过外国人。每个人看到我们都相当惊讶。伊莱不得不担任翻译,他是唯一一个能说两种语言的人。
这位做建筑工人的年轻人,以及村里、他家里的其他年轻男子显然也都外出打工了。村里有几栋新建的房子,包括他家的。我清楚地记得,他家有新的室内给排水系统,他们为此感到非常骄傲。
那天下雪了,他们一整天都开着门窗。我们穿着冬天的外套,但保暖性不够,我们冷得不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窗户和门都开着,但他们告诉我们,那样更健康。
我们不停地跑到他母亲做饭的地方。厨房在一个户外的小棚子里。她一整天都在那里做饭,一道又一道地做。他父亲一整天都坐在炉子旁边,除了偶尔进来吃饭,一直在往里面添柴火。火非常非常热。我们不停地问,我们能不能出去看她做饭?因为我们想靠近火堆。最后他们明白我们有点受罪了,让我们躺到他父母的床上。他们有一张大床。他们拿来了用毛巾或布包着的什么东西,放在毯子里,给我们取暖。那是相当有趣的一天。
这个年轻人当时住在伊莱所住的公寓楼的地下室里。伊莱有一天碰巧下到地下室,发现那里有数百名农民工住在那里,没有电也没有水。没有供他们使用的卫浴系统。没有窗户。环境非常阴暗。没有真正的通风系统。他们用小煤炉做饭,空气很糟糕。他们住在那里,可能是非法的。那不是一个应该住人的地方,很明显它不合乎标准。这就是伊莱开始对农民工状况感兴趣的原因。
伊莱和这个年轻人发展友谊可能至少有几个月了。一开始我们还想,他一定把我们看作是有钱人了,也许他想见见我们,带我们去他的家乡,看看我们是否可以捐助。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没有提出任何类似的要求。他没有向我们索取任何东西。他们继续保持着友谊。不过,我想他没能继续和那个年轻人保持联系,伊莱结束语言学习后就离开了,有好几年没有再回中国。
伊莱开始了解到农民工的情况,并认为他想知道更多。所以当我们再次回去时,我开始接触各种人脉网络,以便能见到一些可能帮助我们了解情况的人。随后在香港、广州和北京,我们接触了相当多的劳工学者、劳工记者,以及一些活跃于这些NGO的人。我开始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而且伊莱和我都被彻底迷住了,这使他决定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中国的劳工问题,也使我们开始考虑再次回来,而我们后来确实也回来了。
正是因为我们在那里建立的关系,才真正引向了后来的一切。我们认识了一位名叫陈佩华(Anita Chan)的香港学者,她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澳大利亚。她写过很多著作。她和她的丈夫安戈(John Unger)是后革命社会建构领域的顶尖学者。佩华尤其把注意力转向了农民工的处境,她的书叫《被侵权的中国工人》(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Exploitation and Abuse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她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她帮助伊莱找到了学术上的方向,并且成了他很棒的导师和支持者,然后她帮忙把我介绍进了人脉网络中,认识了香港和大陆劳工运动中的许多人,这又引向了下一次(访问),最终我自己去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较长访问,在 2003 年和 2004 年去过好几次,最终我们去进行了一次为期六个月的更长的访问,我想那是 2006 年 2 月,中山大学的春季学期,那是我们第一次在中山大学教书。